一九六九年的春天,一个孙姓的上届同学,从驻营口的“六零”军队医院偷出一只军犬幼崽,并把它带到了他所下乡的瓦房店以西约百里之遥的狮石屯。
在那个年代,军犬、警犬,可是犬中贵族,狮石屯青年点有军犬的消息不胫而走。
有过养警犬经历的我,心是痒痒的。
当年的秋天,又传来了这只军犬被青年点弃养,送到当地村民家将被宰杀的消息。
救军犬并拥有它的信念,立即升腾于我脑际。于是,自掏腰包买上三十斤苞米,邀上本点的丰姓同学,辗转三十华里的崎岖山路来到了狮石屯,用粮换狗。
狮石屯儿与長兴岛隔海峽相望,该屯与我所在的左屯一样的贫穷。
一进屯儿,就见到乱石堆砌的墙上,用白石灰画满了一个接一个的圈儿,那是当地山民为吓唬狼而画。据说,野狼经常光顾该屯猎杀狗、猪和鸡、鸭,当地人世代都处在恐狼的阴影中,可见此地之偏僻和荒凉 。
经下乡到狮石屯的营口同学引荐,我俩气喘嘘嘘地来到那个准备杀军犬的农户家。

这家男主人四十来岁,黑红的脸膛儿,削瘦的中等身材,着一身满是补丁的旧衣裤。其家有破败的三间石砌房,室内杂乱,石屋儿被火油灯熏得乌黑的四壁,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。
朴实的男主人说:“你们如果晚来一步,我就把狗杀了。”
我说:“大哥,那狗呢?” 我的话音未落, 院里传来一阵阵狗的轻柔哀鸣声。
我俩遁声望去,只见一只茶色的中型的半成年雄性瘦狗被栓在枣树杆旁。这是只短毛狗。只见它身材削瘦,半耷拉着双耳,嘴巴乌黑,后腿儿带蹬儿,前额宽大,两眼机警,像似时刻听从和揣度主人的指意而蓄势待发。那股机灵劲儿,超乎我平生所见到的任何一条狗。它与我们平常所见到的什么笨狗、土狗丶洋狗丶巴狗、猎狗之类截然不同。
狮石屯的同学指着这条瘦狗说:“就是这条狗,我们管它叫‘赛虎‘ ,是孙xx从营口军队医院偷来的。青年点儿的粮不够吃,它自小到现在都营养不良,耳朵都没竖起来,还瘦。又不忍心杀它,只好把它送给了老乡儿……”
我和丰同学警惕地走近了军犬,说来也怪,这只与我们素未相逢的狗,一反生狗遇生人就狂吠之常态,非但不对我俩示威,反而对我俩抿着耳朵、摇着尾巴极尽亲昵和示好之态,其嘴里还不断地发出呜咽的哀鸣,着实令我心生怜爱。
这只狗的当时表现也太令我俩意外了,难道它真能预知我俩跋涉三十里山路,专门来拯救它一命吗?!
不再有犹豫了,我回头对那老乡说:“大哥,这三十斤苞米换狗,行吗?” 老乡大哥立马儿同意说:“行,行!”
我丢下米袋子,直接把狗从链了摘了下来,再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栓在狗脖子上。与狮石的同学和这位乡作别后,牵狗回返。
这只军犬,不但顺从地跟着我们往外走,而且对于我俩像见到了它久别重逢的旧主儿似的,竟站起身来,前双腿抱住我的上身,扭腚、摆尾,舌舔,极尽亲眤之态,一时把我俩弄的不知所措了。
还栓它干啥呀?解绳子吧。
于是,我俩索性解开绳子,任其奔跑。
按常识,狗被生人牵出家后,再放开它的第一反映是回家寻旧主儿。而这个军犬真是一反狗之常态,竟乐愿跟随重未见面的新主人走出山屯儿,真的令人费解了。
这狗四处撒欢儿,兴奋得象个孩子。它似乎知道了自已得救了。
值得提及的是,我和丰同学同时接触的这只军犬,可它却偏偏对我更亲。它一路狗颠儿,忽而奔向草丛,忽而跑到山崖;时而巤毛耸立,时而对一堆什么兽儿拉的糞便嗅个没完儿。
三十里的归程,三十里的人、狗情,我俩一路上欢天喜地、心境像一样的阳光般的明媚、幸福满满。
回到了青年点,这只军犬仿佛回到了它久别的家,竟没有一点儿陌生感。也正是由于它的机灵和友善,以及它的血统的高贵丶稀缺,很快就赢得了同学们的一致的喜爱。
为了是否给狗另起名儿一事,同学们经过激烈的讨论后,多数人认为还是延续它的旧名——“赛虎” 。
“赛虎“的到来,给同学们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乐趣。诸如,什么抛物取回呀,坐、卧、立、行呀……这个“赛虎”是一教就会,绝不含糊儿。 一时间,青年点竟成了训犬埸了。
青年点有军犬一事,也吸引来屯内老乡们的好奇。他们纷纷来品赏它。见到我们花样翻新地训狗,以及这狗接受能力强丶领悟学习项目快,懂人语,性格温和,善于领会主人意图,机警伶俐等异乎当地土狗的先天秉斌,赢得了 当地老乡们的交口赞誉。至于这只军犬之所以比当地任何犬种都聪明丶机警,並能准确地领悟主人意图的成因,只有一种解释:那是由于血统决定的。
当年,未成年又不谙世事的我们,又豈能不教“赛虎”恶作剧呢?
于是,由一开始教唆“赛虎”咬猪、袭牛、追驴之类的科目,到后来又教唆“赛虎”去猎鸡、捉鸭、擒鹅了。
这“赛虎”自然是唯命是从、乐此不疲了。于是,开始帮我们做坏事了。捉鸡、捉鸭、捉鹅……“赛虎”从不合糊,不折扣。
这与其说是“赛虎”的“成
绩” ,还不如说是我们的“恶作剧”。 很快,在当地农人的恼怒中,我们自知犯错了,于是,立马收手,停止作恶,尽力挽回坏影响。
虽然同学们都爱带“赛虎”去玩儿,但只要是我在场,这”赛虎”只唯我命令是从,无人能引诱得去。
为此最为嫉妒的,是与我同去解救”赛虎”的丰同学和为我们做饭的左大伯。
丰同学大惑不解地对我说: ”这狗,是咱俩一起去三十里之外把它救回来的,它咋就对我不亲呢?”
左大伯自以为:“我每天三顿地喂‘赛虎‘,那‘赛虎‘一定是最该听我的指令的。”
为了检验“赛虎”对他的忠诚程度,左大伯就当着大家的面儿唆使“赛虎”咬我。
这”赛虎“呢,先是瞅瞅默不作声的我,再看看向它发出指令的左大伯,霍地从地上站起来,耸着耳朵,竖起脖颈巤毛,低吼着,呲牙咧嘴地直奔左大伯。”赛虎”毕竟是兽儿,它可是真咬啊!
养了一辈子狗的左大伯见这兽对他动真咯儿的,吓得脸儿变形儿,差声儿变调儿了,狼狈地爬上了炕,操起烧火棍历声呵斥这个喂不熟的“白眼儿狼”,惟恐躲之不及。这一闹剧般的场面不仅让左大伯颜面尽失,还让同学们乐翻了天。
而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一一当年深秋,我只身去前街的友人左春石家摘枣儿吃。不曾想,左春石家的大黄狗发了疯般地冲上来咬我。当时可把我吓坏了,因为这只大黄狗是出了名儿的凶恶。我一边声嘶力竭地呵斥大黄狗,一边向左春石的家人呼救。
左春石的小脚儿老母亲急忙从屋里赶来,大声训斥她家的大黄狗。然而,这只发狂的大黄狗全然不听女主人的禁令,非要咬到我这个“贼人”不可。当时,我被这只大黄狗逼在枣树下,面对恶狗的穷凶极恶,我只好一边用树技子抽它,一边向人们歇力地呼救。
而这大黄狗是毫无惧色,是愈打愈凶,张开大嘴,呲着长牙,非要扑倒嘶咬我不可。
就在这危难时刻,身在二百米之外青年点中的”赛虎”,听到了我那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后,火速赶来,义无反顾地冲向大黄狗,遂与大黄狗厮咬成一团儿。
大黄狗是屯中的狗霸。平素,屯中的公狗都躲着它走,它更是对屯中的母狗们拥有绝对的优先交配权。而这瘦弱的“赛虎”,又怎是它的对手呢?没经几个回合的较量,大黄狗就把“赛虎”按倒在地,猛力嘶咬“赛虎”,边嘶咬、边摇头发力、边怒吼,大有把“赛虎”置于死地之势。
“赛虎”在大黄狗的身下无力地抵抗着,哀号着,其状极惨。
我见状,哪顾什么人的尊严,冲上去一把拽住大黄狗的后腿儿,开始拉狗打仗的偏架。
那大黄狗见我拽住它,刚一松口,“赛虎“立马儿缓过劲儿来,跃起身来,张口咬向大黄狗的喉咙。这时的大黄狗哪受这个窝囊气,恼怒得更加疯狂。然而,它是有心无力啦,它的两条后腿被我牢牢拽住而无从发力,它咬不到”赛虎”,只有被咬的份儿,气得大黄狗眼瞪如灯,怒火中烧,声嘶力竭…
“赛虎”在我的庇护下,没有受太大的伤,大黄狗也因为是在我的干扰下,也没占多大的便宜。
所幸友人左春石闻讯从生产队的牛圈那赶到,才解了“狗围”。
惊魂未定的我,抱着浑身是伤的”赛虎“,连声对左春石母子说:“对下起……”,然后狼狈地开了“案发地”。
在回青年点的路上,我抚摸着“赛虎”的伤口,百感交集,两眼噙着泪水,由衷地感戴”赛虎”。“赛虎”它明知自己不是恶霸大黄狗的对手,还舍命与之相搏,解救我于危难之中,其忠主报恩的义举,令我镂骨铭心。
转眼,到了腊月。同学们三、五结伴地回营口与家人团聚去了。可是我却舍不得丢开”赛虎“。
家里已来信催了,问我几时回家?未成年的我心理极其矛盾:一边,是与久别的亲人年终团聚;一边,是我心爱的孤独”赛虎“无人伺养,着实两难啊。
又捱了两个星期,终于到了年根儿了。做饭的左大伯见我整日不堪的样子,就开导我说: ”孩子,你放心回家吧,“赛虎”呢,我伺养它。实在不行,就它带回我家。我家的大黑儿是母狗,公、母儿不打仗,你要实在不放心呀,就过完年就早点儿回来…… ”
我听了左大伯这么一说,郁闷的心情像似开了两扇门似的豁然开朗,在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感激中紧紧抱住左大伯,就差给他叩头了。
我忙说:”我 回家住不了几天,尽快回来。”
于是,决定第二天返家。
第二天,左大伯早早就来到了靑年点,先为我做饭,再帮我打点行李。
与其说是行李,不如说是用棉毯子包裹地瓜、苹果等一百三丶四十斤的食物包儿。
因为我的城市户籍早被国家注销,家里没有我的口粮啊。
该出发了,左大伯用独轮车推着我的行李,送我去四里之外的火车站,”赛虎“呢,也紧随着我,它围着我,在我身边跑前跑后地与我耳膑厮磨。一会儿嘴叼我的衣襟;一会儿立起身来用嘴舌狂吻我的脸;一会儿又象个孩子般的与我撒娇儿。这一上午就是粘着我寸步不离。
在露天儿候车点上,“赛虎”或以它的第六感观知道了我要离它远行。只见用它那它那茶色的眼珠盯着我,嗚吟着,可怜兮兮地叼着我的棉衣,一会儿又立起身来猛舔我的脸,生怕我抛弃它,离开它,像是与我作生离死别。
一条狗这般地粘着我,也引起了候车的旅客们的注意。因为,在当地的土狗是不会像“赛虎”这般粘人的。 围观的人议论着,七嘴八舌地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。此时此刻的我的内心是极其矛盾的、挣扎的,心如针扎般地难受。因为它不仅是一只十分难得的纯正的军犬,是我的好朋友,还是舍生忘死救我于危难中的义犬。
我抚摸着赛虎的头,安慰它,告诉它——我不久就会与它再聚的……
远处的火车呼啸而来,又徐徐地停下。左大伯费劲地帮我从独轮车上抬下约一百三~四十斤的行李包儿,再协助我把行李抬到火车上。
暂短的三分钟的停车时间到了。我踏上返乡的火车,一边与左大伯道别,一边忍忍地招呼着”赛虎”。
这时的”赛虎”,死死地叼着我的棉裤不撒口,急得左大伯用力拽开“赛虎”,以防发生意外。
火车随着气笛声声缓慢地开动了,我探出车窗向左大伯和”赛虎”挥手道别。这时的”赛虎,“误以为我招呼它,发疯似的边狂吠边追赶火车,可怜巴巴地望着我,它似乎在说:“主人,你咋忍儿把我丢下自己走了呢?! ”
这时的我,哪还顾着上斯文?强忍泪水,大声命令”赛虎”一一回去,回去……
火车驶进小李屯的山峽了,渐行渐远的“赛虎”已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儿,随即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。
归家后,我的心里一直放不下“赛虎”。没等到正月十五,就不顾父、母的再三挽留,只身回到了冷清的青年点儿。
做饭的左大伯闻讯来到青年点,没等我询问”赛虎“的情况,就脸色难看对我说: ” 孩子啊,自你头年上火车回家,那“赛虎”就随着火车追你,不管我怎祥呼喊,它连头儿也不回。当天晚上挺黑了,“赛虎”才回到青年点,我把它领到我家。它吃饱了之后,又跑出去车站找你去啦。打那以后啊,它只来我家三次,每次都是呆不大一会儿,就立即往火车站方向跑。再后来,就不见了“赛虎儿”的踪影儿…… ”
我没容左大伯说完,就一个腚墩儿地坐在冰冷的地上嚎啕痛哭了起来。
我抱怨左大伯,我悔恨我自己,我接受不了失去“赛虎”这个残酷的现实。
“赛虎”走了,永远地走了,这一辈子,我也再见不到我那心爱的,有恩于我的“赛虎“啦。
时光荏苒,半个世纪过去了。在这漫漫的岁月里,我都一直怀念着它。至死,我也不会忘记这只舍命救我于危难中的军犬“赛虎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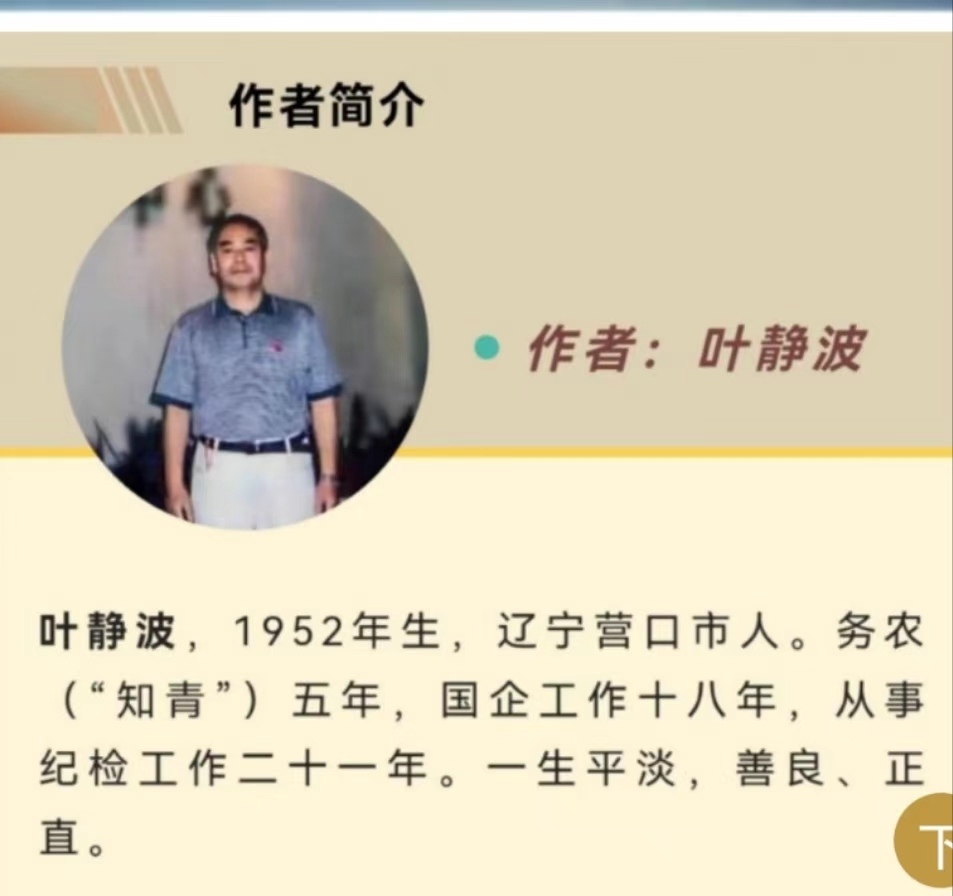
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