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条土路像僵死的蚯蚓一样顺着兰草河向北延伸,路的东侧是兰草河,西侧是农田、农舍。在竹园生产队和大箭杆沟口处各有一块三四亩大的苇园,密匝匝的芦苇绿得飞扬跋扈。太阳一落山,单身路过苇园时,惊恐得让人心跳不止,生怕从苇园中跳出一个女鬼,摄人魂魄。
过了大箭杆沟的河,土路又转到农田中间,路的两边被农人见缝插针栽上了柳条。这种柳条的命运像韭菜,是编簸箕、笸篮的好材料,年年秋季被刈去,编成农具。
如果从空中看,把土路当做竹棍,兰草街上的房子像是串在竹棍上的面筋。这条古老的街道地面上是铺着从河里捞出来的瓦青色的石片,两侧的房舍三面土坯,临街是木板门。我印象中当时供销社与医院的房子略好一些,在这两处工作的人是每月夹着布袋用粮本去粮店买细粮吃的。中街的老买家的房子略好一些,其他的房子稠得一间挨一间,大多是两户共用一堵山墙,房子老旧得像老太太牙疼时扭曲的黑脸。
兰草街的街头是几座铁匠铺,铺门大开,火星闪着亮光往外迸,过路的人像过封锁线一样快速择机通过,生怕沾上火星,把衣服弄个香粗的洞洞。铺子里师傅的吭声与抡锤的徒弟的嗨声交织成一首劳动的乐曲。傍晚时分,师徒三人坐在木门板上,对着一坛老烧酒,吼出一阵闷雷式的猜拳声。
再往北行是供销社的杂货门市,与之斜对门的是卫生院,卫生院临街处是药房,药房的草药溢出的药味很好闻。夹在这两处中间是一棵三人合抱粗的古槐,兰草学校关帝庙院内也有一古槐,树型极为相似,像一对孪生姐妹。据说小箭杆沟口也有棵古槐,五七年毁于洪水。传闻兰草的古槐是从山西洪洞县来的移民,为纪念移民出发地的那棵大槐树所植,这样算来该有七百余年的历史了。可惜这两棵槐树在文革中,被兰草籍的一公社干部煽惑了公社领导,被伐掉了。伐树时只有村民董泽芳出面据理保护,可惜胳膊扭不过大腿,没有保住。街道的槐树下一古井,井水甘甜,井口镶嵌一麻子石做的石圈。是兰草街的水源,现在用上了自来水,水井已束之高搁,但兰草人保护得很好。
那时的兰草学校迎面是一歌舞台,后墙面向街道。三间歌舞台是宫殿式的建筑,结构精奇雄伟,一双人合抱粗的六七丈长的松木檩条是架在前檐上,几块雕花木门,唱戏时卸下是歌舞台,平时安上就是教室。舞台的两端是耳房,耳房结构奇巧,正六边形的窗子。是演员休息与化妆的地方,后来做为教师的住室。耳房下一硕大的门洞,是学校的大门,石墩子上有两块三寸厚桦梨木门板,门常年不关。
这就是我上的学校,这就是我上的初中所在地,我的人生之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我在山神庙小学经毛学文老师、周宝玺老师的悉心教育下,是优秀生。到了兰草街上五、六年年级时沦为差等生了。只因那是到了动乱的初期,学校秩序大乱了。教师人人自危,没人敢管学生了,生怕陷入不测。教我数学的郭崇本老师,胖胖的脸上戴着一幅厚厚的近视眼镜,他一上讲台,学生中几个张扬的痞子蛋就大呼:打倒黑帮分子郭崇本。学生的呼声震天动地,山呼海啸。吓得老师畏缩不前,魂飞魄散,头上直冒冷汗,哪有心思教书?倒是学校有一男一女两位张老师,善演《老两口学毛选》。演技颇高,唬得学生一愣一愣的。学校有位老师叫李健康,教学水平极高。因为是地主成份,他还有一台袖珍式的收音机。学生批斗他是收听敌台,这在当时可是要置人于死地的可怕罪名。
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,断断续续上完了高小。这两年除了穿破了几双鞋,个子又往上蹿了一大截,肚子里没学到啥东西。六年级学完了,学校停了课,后来干脆把门也关了。我被迫回家当了牧童,赶着黄牛,以青山为伴。头顶着蓝天白云,脚上染着牛粪,为农业生产出了点力,没有白吃饭。
在那个时光,每当我坐在山巅,手拄着赶牛的鞭杆,望着山谷里薄岚如烟,见黄牛一边甩着大尾巴,一边斜乜着酒杯大的眼睛咯嘣咯嘣啃草,就心乱如麻。难道我的少年就注定以牛为侣,与青草牛粪为伴度过?想到这里,我好不甘心啊,忍不住胸腔里一阵哽咽。我翘首频频张望校园,山重水复,校园难见,惟闻钟声悠扬,那是给小学生响的。我的求学梦,我的初中在哪里?
过了半年,在这半年中我赶着牛煎熬了一段时间,老师下乡通知学生返校。学校就像封门已久的饭店又开业了。这时学校升级了,改为兰草初中,是小学戴帽子的初中。我放下了朝夕相处了半年的牛皮鞭子,屁颠屁颠地入了学,成了位初中生。
这次兰草的初中把近三届小学毕业生像用笊篱打捞一样捞出来,弄了个一锅烩。学生高矮不齐,年龄参差不等,齐聚一个教室。有的男生唇上已兼兼有了髭须,还有几个女生已前胸鼓鼓涌涌的。我的年龄在不大不小中间,与大个子学生在一起上体育课,一节课连篮球皮摸一把都不可能。
那是个突出政治的年代,只要胸口戴个纪念章就特别风光。在我的苦苦哀求下,母亲卖了鸡蛋,给我买了一枚伟人像章,我戴在左胸前,觉得如挂着一块勋章,格外荣耀。我仿佛浑身充满了力量,充满了温暖。连走路的姿势也变了,像麻雀一样,一跃一跃的,走的是雀步。进了校园,一位高我一头的女生拦住我了,让我把像章给她看看。我见这位女生又高又胖,是个女汉子,如果动起手来,我恐不是对手,只好卸下像章给了她。她把像章用手一捏说:“我不给你了。”当下急得我面色通红,全身的血像是要从毛孔里往出迸发。那女的像猫戏老鼠一样说:“急了吧,急了吧。咦!脸也红了?给你,小气鬼!”她的意思是让她白白拿去我心爱的像章是顺理成章的事,见我愤怒地不甘屈从,就送了我一顶小气鬼的帽子。像章终得于完璧归赵,摆脱了她的魔爪,我再不敢在学校炫耀了。
这时的校长是郭增福。他是位中年人,脸上常带着夸张式的笑容。他一笑就是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那种大笑,是国家级的大笑。他的腮帮子上有浓密的胡须,脸上皱纹很稠。他如果不笑,表情凝重得像足球场边上的教练,一幅老谋深算、鬼神不测的神态。
郭增福,兰东人。早年是卢氏一高的高材生,文理科皆佳,体育成绩也好,但中途退学,未参加高考。多年后我也成了老师,与他在同一学校工作,问及他退学的事,他仰天一笑道:“想学李准嘛!”李准是河南五十年代崛起的名作家,是文学青年的楷模。郭增福原来是心怀文学梦的青年。可惜李准没学成,连王汶石也没当了,当了园丁。他为人从善,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
经过郭增福的拨乱反正,学校结束了混乱局面,逐步走向了正规。学生得以安静地坐在教室潜心学习。当时班级的编排按军事化要求,我这一届分为一排、二排,我在一排,我的好友苗来锁在二排。排里的学生多为农家子弟,衣服上常缀着五颜六色的补丁,脚上还穿着草鞋,纨绔子弟鲜有。那时口袋里的零食顶多是红薯干,偶尔有块馍就觉得特别有福气。
兰草虽然办起了初中,真正胜任初中教学的老师却不多,教师走马灯式地换,所以一段时间学生也学不到啥知识。这时兰草中学老师中的主角登场了,两位青年教师进了校园,挑起了大梁,使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,水平大幅提升,真正像个初中。这二位老师是:郝文战、丁宝玉。
郝文战教几何,他数学功底深厚,教学造诣颇深,课上得风趣幽默。还常常吊学生的胃口,故弄玄虚,在学生百思不解时,亮出思路,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兴趣。丁宝玉老师,兰草街人。他身材修长,面若敷粉,是《三国演义》中周瑜式的人物。那时他正年轻,在高中文理科成绩颇佳,是老三届的优秀生。可惜时运不济,高考停止,与大学失之交臂。丁老师教学能循序渐进,谆谆善诱。我是在他二位良师的教育下,数学成绩有了质的改观,多年后我也步了老师的后尘,成了一位数学老师,同在官坡中学效力。那时的官坡中学数学教育在全县乡镇级的独树一帜。
教语文的是裴喜敏老师,他个子不高不低,眼睛不大不小,脸也不白不黑。头上的头发根根直立,有点怒发冲冠的意思。那时的政治、语文课不分,裴老师对淡如白开水的文根本不讲,比如《南京长江大桥》一文,他不讲,但要求学生会背。学生背,他耷拉着眼皮,像鲁迅笔下的老学究在背《三垂冈赋》中“玉如意,指挥倜傥,一坐皆惊;金叵罗,倾倒淋漓,千杯未醉……”
裴老师对《黔之驴》《曹刿论战》讲的头头是道。他讲得唾沫四溅,口若悬河。
教物理、化学的是孙全安老师。孙老师方面大耳,上课爱吐唾沫,啪啪吐个不停。因为学校没有仪器,实验无从谈起,孙老师只能凭空地讲,讲着讲着没法讲,就干脆来个死记硬背。只要会背,也能考出好成绩。现在想来搞笑,那时学校没有电,像电流表、电压表让学生一看就懂,可惜没有,神秘得像原子弹一样。
就这样,在以上几位老师的悉心教育下,在郭增福校长的管理下,学生总算静下心来学习,后来大部分学生升入高中,在高中成绩也很突出,皆赖以上老师之力也。
班里几位年龄大的学生,一个男生六〇六矿上招工去了,一个戴着红花参了军。两个年龄大的女生,前胸傲人地翘着,翘得让人心馋。望一眼,心里急得像饿虎一样,有急于扑上去摸一把的念头。这俩女生还是个大腚,腮帮子上印着朝霞一般的红晕,两眼中还忽闪着秋波。二人书包里装着布鞋底子,手腕上缠着蓝色的手帕,早自习时一边背书,一边掏出鞋底子“哧溜、哧溜”纳几针。有好事的学生就低声问:“给女婿娃纳鞋底子呀?”女生脸飞红云不语。一个男生指着一位白胖的女生说:“两个蝇子摞在你脊背上沓蛋呢!”女生红着脸过来打。男生打不过,就骂她给野汉子做鞋。
没想到这两位女生,个子大,脸皮却薄。她们受不了同学不怀好意的辱骂,二人找到避静的地方,壮烈地抱头大哭一场,二人起誓相约同时退学。第二天早上,二人来得很早,偷偷把教室扫得干干净净,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五个斗大的字:劳动最光荣!二人默然退学了,含泪回村去农田里劳动。
几年后,我高中还未毕业,其中的一位女同学背着吃奶的孩子,找到我想寻本书看。我翻出一本《杨业归宋》的连环画,她看了封面说:“我不看封、资、修的书。”拿去了一本《夺印》,如获至宝去了。看来她追求文化的欲望并未泯灭,只是身不由已罢了。
当时提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,怎么管理?上级也没有具体的要求。学校就联系村支书让找位贫下中农来学校上政治课,搞点忆苦思甜什么的。对这种摇唇鼓舌就能拿到工分的事,躬耕于畎亩的贫下中农自然轮不到,村支书就代劳了。那个村支书瘦个子红脸,经常来给学生训话,他的脸上带着政治家的气魄,大话、假话一套一套地从他长着黑牙的嘴里往出迸。学生站在烈日下,毒辣辣的阳光像后娘的眼神,格外刺人。支书讲得欢实,学生如同受刑。
经过一年的学习,我的学习进步了,由于我的虚荣心与小聪明作祟,常在班里搞点恶作剧什么的,多次受到老师的指责。我在班里认识的学生也多了,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叫马群英的女同学。马群英住在兰草街,她身材纤细,面含春风,脸上常挂着自然亲切的笑容。这世上的笑脸是女生最好的美容药,最上乘的化妆品。古人描写美女笑脸的诗文很多。比如:一笑千金值;揭窗扶镜看笑靥;回眸一笑百媚生。还有一笑倾人城,二笑倾人国。可见笑脸对女孩子多重要,而且有多大的魅力,马群英的脸上常带着这种笑容。
一日,轮到我当值日生时,我去河里打水,在往河边去的巷口站着窦哑巴。哑巴身材精瘦,他赤裸着上身子,瘦脸上一张夸张的大蛤蟆嘴,嘴里叽里呱啦说着谁也不懂的鬼话。他是我最骇怕的东西。我只好去水井里打水,谁知水桶“嗵”的一声掉到井里。我急得像蛤蟆一样爬在井边往下看,只见那个铁皮水桶漂在水面上转圈圈。一时急得我如坐针毡,全身冒汗,我的大难临头了。这时马群英轻移莲步过来了,她问我:“咋不回家?”我说:“把桶掉到井里了。”她伸长脖子一看笑着说:“这有何难,我能捞出来,只怕女孩子下井被人笑话,我捞过好几次桶呢。”我听了大喜,她脱下鞋子交给我,就像壁虎一样沿着井壁下去了。
她帮我捞出水桶,坐在井沿上穿鞋。那一刻一缕阳光照在她的脸上,只见她浓密的刘海下,一双明亮的眼睛格外得迷人,美丽。
不知不觉到了冬季,这个冬天出奇地寒冷。一天,我缩手缩脚走进教室,见教室的后排坐了一位新同学。这位同学身材瘦弱,头上扎着麻花辫子,身穿一件蓝色制服袄,脖子上围着一红色的围巾。只见她目含秋水,面带蹙容,是那种让人望一眼就忘不了的姑娘。我心中惊奇,一坑蛤蟆叫,咋来了这么一位好同学呢?
原来她叫杨建辉,兰草凉水沟人。其父是南下的解放军战士,在云南成家立业,是某矿山的保卫干部,在文革动乱时被迫害致死。她随其母返回老家,善良的凉水沟人给了她家口粮,杨建辉来兰草中学学习。让人可叹的是远在边陲的云南还是重灾区,出了这么大的事件,让她千里迢迢回到老家。兰草的气侯、风俗与云南相差极大,她在云南学的教材与兰草用的教材大不相同,唯独她的语文成绩奇好。以前我写的作文比不过二排的苗来锁,在一排能独霸江湖。杨建辉一来我不行了,这个小丫头片子!
杨建辉呀,杨建辉。杨建辉生得:蹙眉一双含秋水,玉面笼烟藏春色。她脖子上的红围巾,不知是谁变的?唉!我要是会变身,我就变只漂亮的蝴蝶落到她的头上。
又过了一年多,我的初中生涯结束了。在这所灰蒙蒙的、相貌不扬的学校,让我这个朦朦胧胧的毛孩子开启了人生之路,让我知道了欢乐与悲喜,我的人生之梦开始了!
五十多年过去,弹指一挥间,岁月用无情的风刀霜剑在我们的脸上刻满了沧桑。回首望去,我的同学、我的朋友虽不能像以往朝夕相处,但时刻难忘。我的朋友苗来锁同学是位集大贤大孝于一身的真男子汉,我仰慕久矣!马群英虽久不见面,却常在微信互致问候。曲芹玉是个戏迷,是我老伴的闺蜜。李武同学是我的同事,几十年的交情相濡以沫。还有高个子陈改文、笑面虎姜占营、马秀鸽、夏建设等。班里的乔天成去了县剧团,临别时还送了我一红皮笔记本。杨建辉重回云南,她的母亲四上北京,在冶金部领导的批示下,其父得以平反昭雪。
人老矣,心闲矣!放眼望去,山还是那座山,河还是那道河,川还是那道川,往事皆可忘却,心中惟有不灭的是那团梦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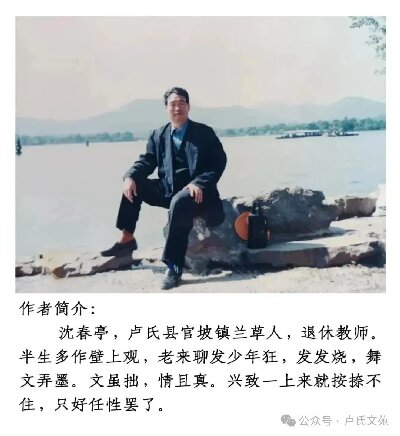
|
